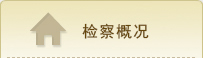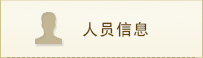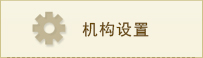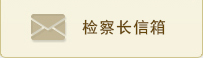自古以来,监狱在人们的印象中,总与暴力、黑暗、腐败联在一起。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法制的不断健全,监狱这座封闭的大门也逐渐向世人“敞开”,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监狱执法也渐趋公正、文明、规范,暴力、腐败现象明显减少,但不可否认的是监狱系统仍然存在一些违法犯罪问题,主要集中在刑罚变更执行环节即为罪犯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执法活动过程中,“钱与刑”、“权与刑”交易现象较为突出。为此,2014年1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2014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启动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剑指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要求重点监督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情况,严查背后的司法腐败。”[1]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该类犯罪的滋生,提升司法公信力,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的现状
(一)监狱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问题比较突出
 图1 2009—2013年人民检察院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情况统计图[2]
图1 2009—2013年人民检察院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情况统计图[2]
从上图表的统计数据可见,检察机关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人数逐年上升,从2009年的9883人上升到2013年的16708人,表明刑罚执行不公正,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问题比较突出。应该说上述数据基本来自监狱,这表明监狱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违法违规现象明显存在,且呈上升蔓延态势。
(二)该类犯罪易发多发,但查处不多

 图2 2008-2012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职务犯罪及本罪的案件数和人数统计图
图2 2008-2012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职务犯罪及本罪的案件数和人数统计图
2008年至201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职务犯罪2341件2752人,其中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180件222人。[3]据此,可推出查处该类犯罪案件数和人数分别约占查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职务犯罪案件数和人数的7.69%和8.06%。上述两统计图是据此数据绘制的。从上图可看出,尽管一直以来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是监管场所易发多发的职务犯罪,也是监所检察机关重点查办的职务犯罪,但全国检察机关查处该类犯罪的案件数和人数不多,所占比例较低。
二、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持续时间长,呈现隐蔽性,
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刑罚执行制度以及司法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徇私舞弊案,常常给当事人各方都带来好处和收益,受害者往往只是国家,因而缺少单位和公民的控告。”[4]而且侦查人员找相关当事人调取言词证据时,当事人出于“害人又损己”的心理,隐匿事实心态突出,且取证对象多为罪犯及其亲友,对象特殊,取证难度大。同时监狱系统有着相对隔离、封闭的特点,“徇私舞弊犯罪的行为人一般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和较多的自我保护手段,直接或间接利用其职务、地位等有利条件实施犯罪,将犯罪行为置于正当的职务行为掩盖之下,作案手段狡猾隐蔽,而且往往案前精心策划案后刻意隐瞒,使得徇私舞弊行为难以被他人察觉,查证难度大。”[5]徇私作为犯罪行为人的内心起因比较隐蔽,且“由于徇私舞弊行为大多发生在一定的专业领域,私情私利交互于亲友、领导、同事等关系之间,”[6]徇私动机难以查证。同时监狱警察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和逃避罪责的能力。因而,该类犯罪具有独特的隐蔽性。
目前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奖罚实行计分考核制度,监狱考核的结果作为对罪犯分级处遇,提请减刑、假释的依据。罪犯要获得减刑、假释机会,需要一定的考察时间,获得一定数量的奖励后才能减刑、假释。而“监狱对罪犯的奖励除了检举揭发、发明创造、抢险救灾、舍己救人等重大立功之外,常规的表彰需要一定的考验期限,短的三五个月,如表扬;长的要一二年,如劳改积极分子。”[7]罪犯要累积到一定数量的奖励需要持续较长时间,相应地监狱警察即使通过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不法方式帮助罪犯获得一定数量的奖励同样需要持续较长时间,这让该类犯罪持续时间较长,有的犯罪被发现时已经持续了相对长时间。
案例一:原辽宁省大连监狱监狱长谢红军等人徇私舞弊减刑、暂予监外执行案。
1995年12月至2001年5月,被告人谢红军在任辽宁省大连监狱监狱长期间,收受罪犯邹显卫的贿赂,指使下属采取虚报和夸大事实的手段,编造邹显卫有检举和立功情况材料,致使邹显卫于1997年12月、1999年3月两次被减刑。此后又为邹显卫编造保外就医的假材料,致使邹显卫于2000年3月21日被决定保外就医2个月。2000年4月7日晚,被告人在得知邹显卫在保外就医期间重新犯罪后,将其收监,但并未采取严格监管措施,致使邹显卫于次日被他人带出监狱长期脱逃。[8]
该案的犯罪持续时间从1995年12月到2001年5月,长达六年,反映了该类犯罪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二)与受贿犯罪交织,呈现交叉性
司法实践中,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中的“徇私”主要是徇个人之私利,即受贿或索贿。表现为监狱警察利用手中的计分考核权、工种和奖励的分配权等进行权钱交易,牟取私利,非法收受或索取罪犯及亲友的财物。监狱警察往往是得到贿赂后,通过违规考核奖罚帮助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同时监狱中不同工种,其考核分的计分基点不同,但好的工种非常有限,监狱奖励也有严格指标,可谓“僧多粥少”。而罪犯觊觎的是能从事好的工种,多拿考核分,比如当值班员、卫生员等;或多拿奖励,如劳动能手、改造积极分子等,从而多获得减刑、假释机会,争取早日“新生”。而监狱警察拥有工种和奖励的分配权,有些罪犯就会不择手段向监狱警察行贿,拉拢腐蚀监狱警察。因而,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与受贿犯罪往往相互交织。目前社会上流传的“提前(钱)出狱”、“花钱买刑”、“有钱的钱服刑、没钱的人服刑”等调侃说法,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此种现象。
案例二:湖北省荆州监狱某监区长许某受贿、徇私舞弊减刑案。
被告人许某在任荆州监狱某监区长期间,于2007年2月、2008年2月、2009年2月、2010年12月多次收受罪犯王某现金共计9000元。在此期间,被告人许某明知罪犯王某在监区内私藏现金和使用手机等严重违监违纪行为,不符合行政奖励及减刑条件,仍故意隐瞒事实,多次建议对罪犯王某给予表扬等奖励,多次为罪犯王某报请减刑,致使罪犯王某被裁定减刑三次。[9]
该案反映出了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与受贿犯罪相互交织的现象。
(三)窝案串案多,呈现群体性
“现随着监狱管理监督机制的逐步完善和刑罚执行工作的分工越来越明细,监狱民警实施职务犯罪往往需要诸多环节的相互利用、协作、靠利益均沾的办法才能实现。”[10]根据司法部《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的规定,目前监狱提请减刑、假释,采取自下而上的程序,其程序如下:

从以上的程序设计来看,“民警单打独斗式犯罪相当不容易得逞,只有通过相互勾结,多人协作,多环节配合才能实现。”案例三:安徽省九成监狱29名狱警腐败窝案
从2007年上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时任九成监狱管理分局泊湖监区第三分监区干部刘某,先后8次收受服刑犯张某及其亲朋现金2.4万元,刘某为帮助张某达到假释条件,将其调换到计分分值高的岗位,并在计分考核中违规为张某加分,使张某获得表扬,提前达到假释条件。
能否申报减刑或假释,由监狱刑罚执行部门确定。为此,张某亲友委托芜湖市民叶某,与时任九成监狱管理分局泊湖监区副教导员的卫某取得联系,2009年上半年,叶某先后送给卫某现金8000元和黄金项链一条。在卫某的帮助下,张某获得申报假释的机会,并于2009年7月被假释。除了帮助张某办理假释,刘某还先后收受其他9名服刑犯贿赂,卫某收受其他13名服刑犯贿赂,给予他们调换工种、办理假释等关照。
安庆市检察院以此为突破口,深入调查,从而撕开了九成监狱隐藏的巨大腐败黑幕,29名干警被立案查处,涉及在刑罚执行方面徇私干警就有11人,他们为近百名服刑人员在调换工种、评劳动积极分子、申报减刑和假释等方面给予关照,谋取不法利益。.可以说,罪犯的工种分配权、每个月实际考核得分决定权以及奖惩权都掌握在监狱警察手中。且“监狱民警集执法、监管改造罪犯和组织罪犯劳动生产于一身,手中拥有对罪犯的监管权、记分考核权、减刑、假释建议权等诸多权力。”/同时监狱对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具有层报权和决定权,监狱完全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其在呈报对象、呈报条件等方面具有“独裁权”;且这种权力的运行处于相对封闭的“高墙”内,公众很难了解其权力运行情况,而内外部监督机制又相对软弱松散,使得罪犯能否获得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监狱警察说了算,这种权力的自由裁量性,不可避免导致寻租空间的出现,为一些监狱警察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寻租,进而违法犯罪创造了条件。
(一)减刑、假释的“供求矛盾”
许多省市都存在减刑、假释比例的最高限制,存在着比例控制,且比例很低,名额有限,应该说是有限“供给”;如自2014年7月1日起实施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实施细则(试行)》第三条规定:“执行机关每年提请减刑、假释的案件数量,一般不得超过在押罪犯的30%(不含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罪犯的初次减刑),女犯可以提高到32%。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减刑可高于规定3至5个百分点。”毫无疑问,罪犯对减刑、假释的“需求”远大于监狱的“供给”,可谓“僧多粥少”。而罪犯对减刑、假释的“需求”是指罪犯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约束条件下对减刑、假释的期望值。司法实践中,符合条件应该得到减刑、假释的罪犯数量很多,同时不符合条件的罪犯也想方设法去获取减刑、假释机会,而减刑、假释的名额有限,实践中出现符合条件应该得到减刑、假释的罪犯因为比例控制和名额有限而未能提请。尽管比例控制有其合理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正是由于罪犯对减刑、假释的“需求”远大于监狱的“供给”,迫使一些罪犯铤而走险,通过不正当途径去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形成减刑、假释的“地下交易市场”,让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犯罪有其必然滋生的“土壤”。
(二)监狱警察权力的自由裁量性
目前监狱对罪犯减刑、假释实行“计分考核、以分记奖、以奖减刑假释”的工作机制,罪犯需要获得一定数量的奖励表扬后才能减刑、假释,如江西省规定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获得月考核表扬十次以上方可减刑。因而,罪犯最希望的是能从事好的工种,多拿分,多获奖励表扬,从而争取早日多获得减刑、假释机会。而“罪犯从事不同工种的生产劳动,考核分的计分基点不同,罪犯每个月计分考核的情况,在计分考核规定之内监狱警察还可以决定实际得分。”
(三)驻监狱检察监督职能作用远未充分发挥
权力的过于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监督,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由于各方面原因,驻监狱检察监督职能作用远未发挥出来。
1.监督手段缺乏强制力。“我国的人民检察院没有指挥行刑的权力,不直接介入监狱的执法活动,它虽然有权监督监狱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可以提出纠正意见,但它没有实体决定权,同时法律也没规定监狱按照人民检察院的纠正意见纠正违法的义务和不纠正的法律责任。”0这种检察监督权力仅仅停留在建议的层面,强制力明显不强,因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监狱对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不理不睬,甚至束之高阁的现象,这严重影响检察监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2.监督触角不深、同步监督不够深入。按照高检院监所检察“四个办法”要求,检察机关对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监督应做到“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但由于各种原因如人少任务重、事前监督的监督对象过于宽泛且针对性不强等,检察机关对监狱的日常管理、考核奖惩、年终评审、狱政部门、大中队研究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以及与此有关的执法工作等很难做到全面全程监督。在计分考核环节,也只是对计分考核结果进行监督,无法对计分考核的过程进行监督。对监狱报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材料也只是进行书面审查,对其材料的真实性难以监督。
3.人少任务重,一些检察院存在着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及“同化”现象等问题。目前派驻监狱检察机关人员少,但对监管活动和刑罚执行监督任务非常繁重,涵盖了从收监、日常管理、考核奖惩、教育改造、刑罚变更执行、释放等全过程。如要对刑罚变更执行实施事前监督,实际上就是要对几乎每一个罪犯的服刑全过程进行跟踪,人少任务重的矛盾非常突出。而且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的派驻检察院或派驻检察人员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有的迫于压力不敢监督、碍于情面不愿监督、疏于学习不善监督,使得驻监狱检察监督的力度和效果大打折扣,难以对监狱刑罚变更执行活动达到预期的监督效果,客观上不能有效遏制监狱警察违法犯罪。同时派驻监狱检察人员一般相对稳定,在与监狱警察长期的工作生活接触中很容易形成熟人关系,有的还结为亲戚关系,逐渐被监管场所“同化”,这难免造成监督虚化。
(四)查处难,惩治力度不够,监狱警察犯罪成本低
司法实践中,“对监管场所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违法犯罪行为,被监管人因害怕被穿‘小鞋’,有损自身利益而不敢讲;监管民警和职工因顾及同事关系及单位的声誉而不愿意讲;监管单位受‘家丑不可外扬’错误思想及‘一票否决’的限制而不能讲。……派驻监所检察人员由于处于监督的地位,被监管民警和被监管人看作‘外人’而小心戒备。在监管场所内形成了以监管民警为主导,被监管人被动服从,对外十分封闭的‘小世界’。”1正是由于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的发案单位、犯罪主体及取证对象特殊,线索来源少、证据隐蔽性强等,让该类犯罪具有较大的隐蔽性,较高的智商性,和其他渎职犯罪一样有着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的共性;且该类犯罪往往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部门所能单独完成的,牵涉面广、层次多,窝案串案多,容易出现责任分散,办案阻力较大等问题。同时目前监狱内部纪检监察监督存在失之于松、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对违规违法警察处罚力度不够;且和其他职务犯罪一样,该类犯罪也普遍存在轻刑化现象。因而,该类犯罪存在着查处难、处罚力度不够、犯罪成本低等情况,难以对监狱警察实施该类犯罪形成强大威慑力。
四、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一)适当提高减刑、假释比例,并在基本控制线内有浮动线,以缓解“供求矛盾”
由于罪犯对减刑、假释的“需求”远大于监狱的“供给”,让该类犯罪有其必然滋生的“土壤”。而要铲除生长出“毒树”的“土壤”,就应适当放宽减刑、假释人数占在押罪犯人数的比例限制,并在基本控制线内有1%到2%的浮动线,以缓解其紧张的“供求矛盾”。对符合法律规定标准,应当依法减刑、假释的,不能因为受比例限制而不予减刑、假释,更决不能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予以减刑、假释,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犯罪的滋生。如江西省规定每年提请减刑、假释案件数量,2014年的规定就比2008年的规定减刑一般不得超过28%(不含死缓犯、无期徒刑的减刑),女犯可以提高到30%,假释一般不得超过3%,提高到了一般不得超过在押罪犯的30%(不含死缓犯、无期徒刑罪犯的初次减刑),女犯可以提高到32%。2014年的规定比2008年的规定提高了2个百分点,这就有助于缓解减刑、假释的“供求矛盾”。
(二)完善罪犯考核奖罚机制,加大狱务公开力度
1.应完善罪犯考核奖罚机制。目前监狱警察在计分考核、奖扣分环节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个体性。如江西某监狱《罪犯考核奖罚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先动手打人的,扣4分,还手的,扣3分,不听劝阻互殴的,各扣5分。但实际上该监狱警察在处理罪犯打架的事情上,一般是各扣2分,而且是扣劳动分,不是扣思想分,根本没有按照考核细则执行,这已经成了该监狱的惯例,这种处理的随意性,给监狱警察徇私舞弊留下了空间。因而,应完善罪犯考核奖罚机制,最大限度地控制监狱警察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集中化、随意化和私有化。具体来说,在计分考核、奖扣分环节,要在程序设计上明确民警个体只负责记载事实,待集体研究并取得相应证据后,再对照罪犯考核细则执行。在处理违监违纪上,明确规定单个民警不得处理,必须两人以上方可处理,并履行报告制度。
2.应加大狱务公开力度,以公开促公正,倒逼监狱警察严格规范公正执法。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让更多的阳光照进监狱,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监狱警察权力的滥用与寻租。目前狱务公开大多只是在狱内、在“墙内”,公开范围有限,公开渠道不畅,公开方式落后。因而,应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大公开范围,畅通公开渠道,创新公开方式。在公开内容上,事关罪犯服刑的内容如考核、奖罚、减刑、假释等需要什么条件和程序及考核结果应予公开;狱政管理活动如怎样安排罪犯的生活劳动等应予公开。在公开范围、方式上,不仅在“墙内”更应向社会公开,不仅要采用张榜、上墙等方式更应运用信息化技术公开。同时更应全面落实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公示制度,拟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提前予以公示,且在公示期间,任何人都可提出异议,对提出的异议,监狱应及时调查,一旦有问题,应及时纠正。而且减刑、假释裁定书及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一律上网公开,同时寄送原办案单位,以增加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
(三)完善罪犯权利保障制度,加强驻监狱检察监督
从上文分析可知,监狱警察权力的自由裁量性为一些监狱警察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进而违法犯罪创造了条件,因而,要有效预防和控制该类犯罪的滋生,应要有效遏制监狱警察权力寻租。
1.完善罪犯权利保障制度,以罪犯权利制约监狱警察权力。目前我国“罪犯在减刑程序中处于客体位置,毫无权利可言,几乎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辩护权、申请权和申诉权等,只能消极地等待结果的到来,减刑并不具备完整的权利形态,法律仅从制度角度而未从权利角度对减刑进行诠释。”2因此应赋予罪犯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上的知情权、参与权、辩护权和申诉权等,如在罪犯认为其应被提请减刑、假释而监狱未予提请时,应赋予罪犯进行相应救济的权利等,让罪犯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程序中有更多的声音。
2.加强驻监狱检察监督。具体来说,应增强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的强制执行力,适当增加派驻监狱检察人员的编制,并实行定期轮岗交流和任职回避制,特别要健全对监狱刑罚变更执行活动的同步监督机制。派驻检察室应与监狱的微机联网实现犯情动态信息共享,依法加强对罪犯的改造表现和计分考核情况以及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同步监督;同时把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检察监督同日常深入学习、生活、劳动三大现场检察监督工作结合起来,并重点监督监狱日常对罪犯的计分考核、奖励表扬、违纪处罚等活动;推进监狱、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减刑、假释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建设,从技术上确保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到位。
(四)加大案件查处和惩治犯罪力度,构筑威慑防线
从上文分析可知,要有效预防和控制该类犯罪的滋生,应加大该类案件查处与惩治犯罪力度,保持打击犯罪的高压态势,提高监狱警察犯罪成本,同时发挥查办案件的预防与威慑作用,构筑威慑防线。具体来说:一是驻监狱检察机关应积极拓宽发现案件线索的渠道,除通过定期开启检察官信箱、发放检察联系卡、开展罪犯刑满释放前谈话、严管禁闭人员谈话等外,还应深入监狱学习、生活、劳动三大现场,对狱政管理活动实行同步、动态跟踪,及时了解掌握监狱警察对罪犯进行日记载、周评议、月考核等重要管理活动,拓宽发现案件线索渠道。同时发挥派驻检察与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联动优势获取案件线索,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后,应克服阻力与困难坚决进行查处,决不姑息,绝不手软,使其“不敢犯”。二是严格限制判处缓刑、免于刑事处罚比例,提高判处实刑比例,让监狱警察脱下警服换囚服,使其“不愿犯”。三是注重发挥查办案件的预防与威慑犯罪即侦防一体化的作用,追求办案效果,防止案结事了。通过以案释法,剖析反面案例的预防宣讲和针对发案特点、成因向发案单位提出的检察建议的作用,有力促使发案单位查找问题、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规范秩序,达到“查案一处、完善一面、教育一片”的良好法律效果,使其“不能犯”。
[1]徐盈雁:《重拳出击剑指“三类罪犯”违法刑罚变更执行》,《检察日报》2014年5月22日,
[2] 数据来源于2010-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3] 参见《最高检将开展专项行动,检察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情况》,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jsxw/201402/t2014024_4742320_1.htm,于2014年7月2日访问。
[4] 张鹏:《查处徇私舞弊类案件的问题及原因》,《人民检察》2001年第11期。
[5]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破解查办徇私舞弊型犯罪难题》,《中国检察官》2008年第8期。
[6]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破解查办徇私舞弊型犯罪难题》,《中国检察官》2008年第8期。
[7] 张耀阳 薛增跃 张宇:《短刑犯监区应专设》,《检察日报》2014年4月7日。
[8] 《谢红军等人徇私舞弊减刑、暂予监外执行案》,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http://www.spp.gov.cn/site2006/2006-03-03/001125104.html,于2014年7月2日访问。
[9] 来源于2013年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鄂沙洋县刑初字第00034号。
[10] 参见李成:《监狱民警职务犯罪防范与控制研究》,南京理工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 参见李成:《监狱民警职务犯罪防范与控制研究》,南京理工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页。
- 《减刑、假释岂能明码标价—一起狱警腐败窝案暴露出的监狱刑罚执行问题》,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2/20/c_11943054.html,于2014年8月31日访问。
. 李禛:《监狱警察职务犯罪剖析-从山东省监狱系统职务犯罪的现状出发》,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
/ 袁其国主编:《监管场所职务犯罪典型案例评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412页。
0 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狱监督制度比较研究”课题组:《我国监狱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法学》2011年第4期。
1 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编:《监所检察工作指导》2014年第1辑,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
2 刘漫漫 冯兴吾:《当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8期。